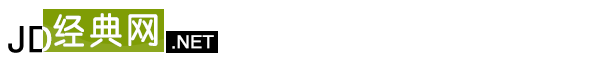丁玲:一个文青的革命之路在线观看「丁玲女作家」
文/何书彬
↑1952年丁玲和陈明、蒋祖慧在多福巷家中
1942年的早春,在延安蓝家坪的一间窑洞里,38岁的丁玲与小她13岁的陈明结婚了。
在此之前,丁玲已经有过三次恋爱经历,并生育了两个孩子。在孤身一人到达陕北边区后,丁玲喜欢上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同事陈明,无话不谈的他们很快发展成恋爱关系。
在去延安前,陈明是上海麦伦中学的进步学生、市中学生救国联合会里的积极分子。在那时向往延安的无数年轻人中,陈明只是其中普通的一个,而丁玲早已是拥有极大声望和影响的知名女作家。
在五年的曲折恋爱之后,二人低调地结婚了。“没有张扬,没有请客。”婚后的丁玲,对邻居“罗老太太”说,她和陈明“爱得很苦”。
也许对种种无形的压力有切身的体会,一个月后,丁玲在《解放日报》上发表了一篇杂文《“三八节”有感》,历数女性在延安的遭遇。丁玲说,延安是革命的中心,每年的这个时候,都“有大会,有演说的,有通电,有文章发表”来庆祝妇女运动,但实际上延安妇女并没有迎来她们想要的解放。
以婚姻为例。在延安,无论一个女性如何做,都会遭受非议,如果她不结婚,人们会视之为“罪恶”;如果她结婚了又怎样呢?那她便不能免除“落后”的命运,“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:‘回到家庭了的娜拉。’”
编辑刊发的时候,丁玲有一种隐隐的不安,她很清楚这篇文章将必然给她招致新的非议,但她当时没有想到,延安的一场风云正在酝酿之中,很快她就将卷身其中。
初遇“娜拉”
丁玲在文章中提到的“娜拉”,是“五四”以来有关中国女性命运的一个象征。 1918年,《新青年》的“易卜生号”发表了剧作《娜拉》,这个独立自主、个性鲜明的“娜拉”在“五四运动”中成为女性解放的偶像。
“五四”风潮到达丁玲的家乡常德时,她却正处在困扰之中,当时她已十四五岁了,与表兄的婚约即将成为现实,看着同学们都热情地组织学生会,到处游行、演讲、喊口号,丁玲一开始很茫然,“她们为什么这样激动呢?”但她很快也被感染了,成为这些激进女学生中的一个。
在《记丁玲》一书中,丁玲的同乡好友沈从文回忆当时发生的一切:“(五四)余波所及扩大到了桃源,就使几十个年约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发了疯狂。‘自觉’与‘自决’的名词、‘独立互助’的名词、‘自由平等’的名词,以及其他若干新鲜名词,在若干崭新的刊物上,皆用一种催眠术的魔力,摇动了所有各地方年青孩子的感情。”
在整个社会的风云激荡中,1922年初,她来到了上海,感觉是进入了“广大的领域里”。她和王剑虹、王醒予、周敦祜一起,四个人合租了一间房子,在四壁空空的房间里打地铺住下。不久后,周敦祜进入一家医院工作,丁玲等则进入平民女校。
“娜拉”的困惑
丁玲极力想证明自己的自立,她开始四处找工作,看到有学校招聘教师或是有工厂招聘绣花工人的消息,她都赶紧过去,但是都无果而终。
1923年,丁玲离开上海去了北京。那时的丁玲过得并不愉快。她的弟弟和最好的朋友王剑虹都在不久前去世了,这使她“感伤气氛极重,大约因为几年来在外边飘飘荡荡,人事经验多了一些,少年锐气受了些折磨,加之较好的朋友又死掉了,生活又毫无希望可言,便想起母亲,想起死亡的弟弟,想起不可再得的朋友,一切回忆围困了她……因此便不问黄昏清早,常常一人跑到最寂寞僻静地方去,或是南城外陶然亭芦苇里,或是西城外田野里,在那些地方痴坐痛哭”。(沈从文《记丁玲》)
1925年,感觉寻求不到出路的丁玲在苦闷中回到湖南老家。有一天,丁玲一开门,就惊奇地发现,她在北京“只见过两三次面”的胡也频找过来了。胡也频是从一所海军学校退学的学生,抱着文学梦来到北京,并在年轻人的聊天中结识了丁玲,在沈从文的鼓动下,他对一见钟情的丁玲开始了热烈的追求。
丁玲与胡也频一道返回北京,在香山租房同居了。他们仍是无事可做,有时竟至绝粮,便去找沈从文,同吃“慈幼院大厨房的粗馒头,次数似乎也很多很多。”几个年轻人都希望以写作来打开一条出路,但是投出去的作品却常常碰壁,他们还尝试着办文学刊物,但也都无果而终。
丁玲一举成名,来自于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,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轰动效应。这篇日记体的小说分为三十多段,运用心理分析的手法,展现了一个追求个性解放,走出家门的青年女性在爱情和理想幻灭后的内心世界。无聊的莎菲在寄身的公寓里以煮牛奶和翻报纸消磨时间,她痛恨和蔑视一切,厌倦那些“才女”写的诗句“悲哀呀我的心”,自己又无路可走;患了肺病后,她便放纵自己的感情,倾心于南洋子弟凌吉士的丰美外表,却又鄙视他卑劣的灵魂,终于陷于痛苦的挣扎之中。最后莎菲决定“搭车南下,在无人认识的地方,浪费我生命的余剩”。
在“五四”退潮、大革命失败的背景下,“莎菲”的苦闷、彷徨、伤感、绝望,让无数的青年人产生了强烈共鸣。正是在这时,丁玲与冯雪峰结识了。
“娜拉”向左转
冯雪峰看了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,禁不住感动得流泪,身为一名男子,他对“莎菲”的理想与爱情的幻灭也极有感触,但是他又说:“这篇东西效果不好,是消极的,看了会使人消极,太空虚了!太消极了!”(丁玲,《和几位文学界朋友的交往》,《我在爱情中生长》,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)
一开始,丁玲只是找冯雪峰补习日语,根本不知道冯雪峰在苏俄文艺理论译介上的勤奋和成就。未几,二人兴致盎然的谈话就取代了原有的补课计划。丁玲深切地感受到与冯雪峰的相处给了她“思想上的满足”,她几乎是狂热地爱上了冯雪峰,认为这是她第一次真正的爱情。回忆几年来与胡也频的相处,她认为那不过是“小孩般好像在用爱情做游戏”;在给冯雪峰的信里,丁玲这样表白,“我真真的只追求过一个男人,只有这个男人燃烧我的心,使我起过一些狂炽的欲念……这个男人是你”。(丁玲,《不算情书》,《意外集》,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版)
丁玲对胡也频说:“我必须离开你,现在我已懂得爱意味着什么了,我现在同他相爱了!”(1937年,丁玲与斯诺夫人的谈话)
但冯雪峰没有胡也频那样的热情和勇气,从不鼓励丁玲离开胡也频,丁玲也无法回避胡也频炽烈的感情和两人已经同居的现实。最终,丁玲与胡也频和好,并把她和冯雪峰的关系定位为“纯粹是同志”。(丁玲,《不算情书》,《意外集》,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版)
中国知识界此时也在重新审视“娜拉”。左翼文学的兴起促使“娜拉”符号的意义发生了更大偏移和转变。在茅盾的小说《虹》(1929年)中,娜拉符号的再次出现,已经含有了批判色彩。主人公梅行素不满于娜拉“全心灵地意识到自己是‘女性’”,要努力克制“自己的浓郁的女性和更浓郁的母性”,准备献身给“更伟大的前程”,“准备把身体交给第三个恋人——主义”。在“革命”的召唤下,梅行素最终完成了“时代女性”的“革命化”过程。
因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而声名鹊起的丁玲,也开始拥抱这个“转变”,就好似她在“五四”时期被“独立”“自觉”等新思想感染一样,丁玲很快把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左翼文学的创作上来了。
1928年春,丁玲和胡也频来到上海。在冯雪峰的引导下,丁玲写出了《水》、《奔》、《田家冲》等小说,与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相比,这些小说开始具有鲜明的“左联”印记。尤其是描写灾民抗争的《水》,在发表后被冯雪峰赞为“新小说的诞生”。
1930年,胡也频加入“左联”。一年后,胡也频被捕,随后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枪杀。接下来,丁玲也正式加入了“左联”,并担任“左联”机关刊物《北斗》的主编。
1932年,丁玲发表了《莎菲日记第二部》的片段,描写莎菲的转变——莎菲并没有“浪费我生命的余剩”,而是与一位热心于革命的青年结婚了,待到这个青年被当局杀害,莎菲自己也成了一名革命者。丁玲让莎菲这位著名的小说主人公与过去告别了,与过去“所有的梦幻、所有的热情、所有的感伤、所有的爱情的享受”告别,“一点不回头”。
“娜拉”到延安
1936年11月1日,丁玲登上了一辆去陕北边区的汽车。作为第一个自国统区到达陕北边区的拥有极大名望的作家,很自然地,丁玲受到隆重的欢迎。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张闻天都赶过来看望丁玲。在一个大窑洞里,中宣部特意为丁玲开了一个座谈会。这是丁玲第一次当着这么多的中共高级干部的面发言,她掩饰不住心情的激动,“讲了在南京的一段生活,就像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”。(丁玲《序<到前线去>》,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版)
33岁的丁玲,再一次找到了年轻的感觉。在无数的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人中间,丁玲恢复了青春活力。但在两年后,丁玲在延安也感受到了“困恼”。虽然在1932年发表《莎菲日记第二部》的时候,丁玲就开始注意到要和自己身上“旧的痕迹”做告别:“也许我还遗留得有许多旧的成分,是我自己看不清,而常常要在不觉之中,反映出那种意识来。”丁玲还借莎菲之口自我告诫,要经常“审判我自己,克服我自己,改进我自己。”但是在延安,丁玲还是不自觉地在她的写作中流露了她的“旧意识”。
归来的“娜拉”
1942年3月8日,《解放日报》的副刊《文艺》要赶制“三八节”专题,尽管中央委员会事先曾作过指示,要求庆祝国际妇女节时重点应放在庆祝反法西斯统一战线,促进中国统一和颂扬妇女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等方面,但丁玲没有理睬这些,仍我行我素,要把心中的想法一吐为快,发表了《“三八节”有感》。这篇文章不符合当时整风的革命氛围,招致了大量批评。丁玲后来承认对她的指责都是正确的。
丁玲开始迅速地放弃她作品中那种细腻的女性意识,开始把她的写作真正放入到革命话语中去。几年后,她写出了《太阳照在桑干河》上,小说几乎是完全按照阶级斗争理论进行写作的。1951年,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。丁玲正式完成了从女性作家到革命作家的转变。
丁玲正式和“莎菲”、“旧的痕迹”和“旧的成分”说再见了,她“脱胎换骨”了。在整风运动的时候,丁玲就曾写下两本学习心得:一本名为《脱胎换骨》,另一本叫《革面洗心》。1950年时,丁玲又含蓄地描述了她当年的那段心路历程:“在陕北我曾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,我在这里开始来认识自己,正视自己,纠正自己,改造自己……我完全是从无知到有些明白,从感情冲动到沉静,从不稳到安定,从脆弱到刚强,从沉重到轻松……凡走过同样道路的人是懂得这条道路的崎岖和平坦的。”
看历史微信公众号:EYEONHISTORY
热门排行
- [网友投稿] 丁玲:一个文青的革命之路在线观看「丁玲女作家」
- [网友投稿] 大专生可以报考在职研究生吗「大专可以直接考在职研究生吗」
- [网友投稿] 穿搭氛围感是什么「色系搭配」
- [网友投稿] 他们在纸上画「某落榜美术生路过」
- [网友投稿] 新年画描绘新生活的画「新年新气象新家新生活」
- [网友投稿] 怀念一棵 桂花树「门前那棵桂花树」
- [网友投稿] 澳大利亚留学展「澳大利亚广告展」
- [网友投稿] 关山月报春图价格「国画大师关山月」
- [网友投稿] 广东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单「广东省公安厅领导名单」
- [网友投稿] 腾讯自走棋\\「新浪微博亲儿子」
经典笑话
- [经典笑话] 定亲
- [经典笑话] 搁 浅
- [经典笑话] 讽刺对客干坐
- [经典笑话] 讽刺对客干坐
- [经典笑话] 嘉兴人
- [经典笑话] 痴人卖羊
- [经典笑话] 文学
- [经典笑话] 兄弟认匾
- [经典笑话] 心在这里
- [经典笑话] 送 匾
编辑推荐
- [网友投稿] 《can U 》「有料」可持续时尚美学展览
- [网友投稿] 国画山水飞鸟图片「绘画艺术欣赏50字」
- [网友投稿] 是谁浮伤了流年的英文唯美语句
- [网友投稿] 时间会教会你怎么与过去握手言和
- [网友投稿] 有些人注定要失去,就像白天再长
- [网友投稿] 小说《逢场做戏》主角:孟童 陈湛(完整无删章节)全文无弹窗免费阅读【笔趣阁】
- [网友投稿] 适合就爱
- [网友投稿] 花呗免息期怎么算(花呗最长免息期是多少天)
- [网友投稿] 《柚子漫画官网韩国版本》免费BL(漫画)韩漫无删减&连载完结阅读
- [网友投稿] 书画文创产品开发「文创画」
- [网友投稿] 忘不掉的不是爱情,是伤害
- [网友投稿] 父母叛逆期「为什么有些孩子从小到大没有叛逆期」
- [网友投稿] 海誓山盟无需太多,陪伴,就是最好的承诺
- [网友投稿] 山西悬空寺 超\\「山西悬空寺悬在西山」
- [网友投稿] 古典伤感唯美句子 最是不胜清怨月明中